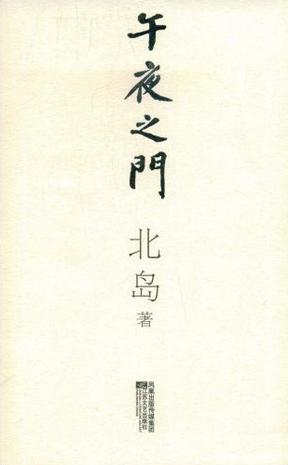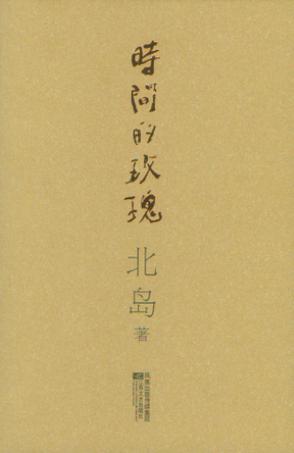走在午夜的街上,入秋,我紧一紧披在身上的外衣,手插入口袋继续向前走着。夜很静,路上几无人影,车偶有呼啸而过。街边的店都紧锁着大门,一些玻璃橱窗深处透出微弱的光。广告灯箱一直亮着,光线稳定而均匀,仿佛自世界诞生以来这光就一直存在着,而世界则永远是黑夜。昼时柏油路积攒的热量在这时挥散开去,形成氤氲的雾气,让呼吸带着潮湿。忽有一人从街边奔突出来,提携着公文包赶上一辆的士,然后消失。转过街角,长长的道路铺向远方的灯火处——夜宵铺子还未收摊,三五人一桌,三五人一桌,喧哗吵闹的声音被湿润的空气吸收尽,就好像眼前所见不属于这个世界一般。走近,地上满是狼藉,等待着清晨保洁人员的打理。空气没有记忆,不能像我述说不久前这里的人声鼎沸。红绿灯机械的变换着颜色,路灯尽责的照着脚下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土地,而光线则极力的向远方穿透。汽车驶过,往日刺眼的远光灯只从行道树施舍给的缝隙中吐出一道道粗细不一的光柱。地面变得潮湿,雾气愈发浓重。走进校园,两旁汽车安静的停着,车上满满都是水汽凝结在上的水珠,水珠越聚越大沿着汽车车窗滑落下来。就好像桑拿房里一个一个静坐着的洗浴的人,沉默,闭着双眼,任毛孔张开,汗珠爬满皮肤。汽车边站着三五个吸烟的人,也是沉默。万籁俱寂,脚下的鞋子和大地轻微的摩擦。雾气下沉更多了,上层的空气变得透明起来。植物也是,枝条叶片都潮湿着,待到清晨太阳升起前的降温就会变成一层薄霜吧。就好似燥热中的隐忍,冷汗。
生活是异乎平静的,平淡。不会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件。我们谈论着,有的,没的。一个个感情色彩的词汇都被时间过滤,最终变成中性的名词零散的被置弃在墙角,脑中的角落。
我极度的不自然的寂寞感,是什么原因。和陌生人的闲谈,和熟识者的寡言,逃避,重生是什么,不过是循环罢了,却被不真实的幻想所吸引。我不相信爱情麽,或许是吧,又或许不是。内心的火欲爆裂出来,我以大声朗读压抑着,找不到合适的出口。我的朗读的声音通过颅骨内的传递以一种和传递给他人耳中不一样的方式传递给我自己,和曾经读此文章的人的声音在那些个特定的词汇,停顿,抑扬上出现共振,然后消散,又共振,然后和作者契合,分离,再契合。
同行的C和G闪烁迷离的笑像是掩饰着什么,我猜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