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认定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不是干净利落的。抱着一种自己也捉摸不透的想法与人交往,寄希望能够长久稳定而安全的保持一个比较紧密的“关系”。这种相对自私的行径不可取也在很多情况下被证明是失败的,彼此皆有可能因为预期和实际不相吻合的彼此心中的位置而产生裂痕最终导致崩毁。当然这在大千世界男男女女上演的无数情感大戏中再普通不过,但或许由于个性所趋真正对于过往情感不能很好“放下”也是束缚自己内心自由的一个原因。
记得某人比喻的好,我在其脑中的印象犹如土块沙石分崩瓦解,然后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相貌、声音、触感、往事很快就都“倒下”了。这个遗忘的过程在开始时显得尤为困难,以至于很多有类似经历的希望忘记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的人,总认为自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沉浸在长久的郁郁中,但最终的事实却是用不了多久,比如十天半个月,当记忆大厦的第一块泥土落下,就注定他会急遽地把过去之事抛于脑后,至少是“真正”放下。很多自认惜古伤怀多愁善感之人皆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昨日便分今日又成的“情场高手”,能拿得起放得下不能说是对感情的不负责,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下一段感情”负责。只可惜自己对周遭感情都缺了很多爽快,就好比往一片吐司上抹奶油,第一层,第二层……每咬一口都混合着过去抹过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味道(话听起来貌似奶油已经抹了很多了,其实没有啦)。结果不但不能很好的品尝任何一种味道,五味混杂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美味,也疲乏了味蕾。私以为这种“享用”方式欠妥,不说对不起了土司,至少也对不起奶油,笑。
如今短时间内似乎也没什么食欲,更少了好好享受美味的时间。以上这些碎语也不单是一时兴起,倒更多是长久积聚的怨气所得?不得而知了。
至于“其他”,本想谈谈志趣的话题,其实自己什么也不懂,若能早熟三年现在的我又有多少区别也不得而知。前些日子又接了人文学院的《表达》杂志排版工作,也算是闲暇时候从英语中跳转出来的一个调节。去年杂志复辟,当时还是自己上手的第一揽活,不知未来还有否机会继续承接这个“任务”下去了。想来似乎也就自己对此还算上心,人文学院的所谓的编辑们也不值得去与他们理论,反倒是给自己编排增添了好几分自由。编纂时候大略浏览了一遍杂志最开头的几篇散文,都不出彩,总还是多局限在个人的小感情小事件里面,缺少一点大气量。倒是两次的人物专栏还有点意思,上次人物专栏——陶科,专程要求竖版倒序排版;这次的高萍,一女流之辈自我简介中也有“平生最恨汲汲功名利禄者、崇洋媚外者、人云亦云者”,又有“叹吾国百年凋零,恐圣心不作,故抛却七弦冷箫,上下求索,‘虽九死其尤未悔’”这般句子,看得颇有羞愧难当、额沁冷汗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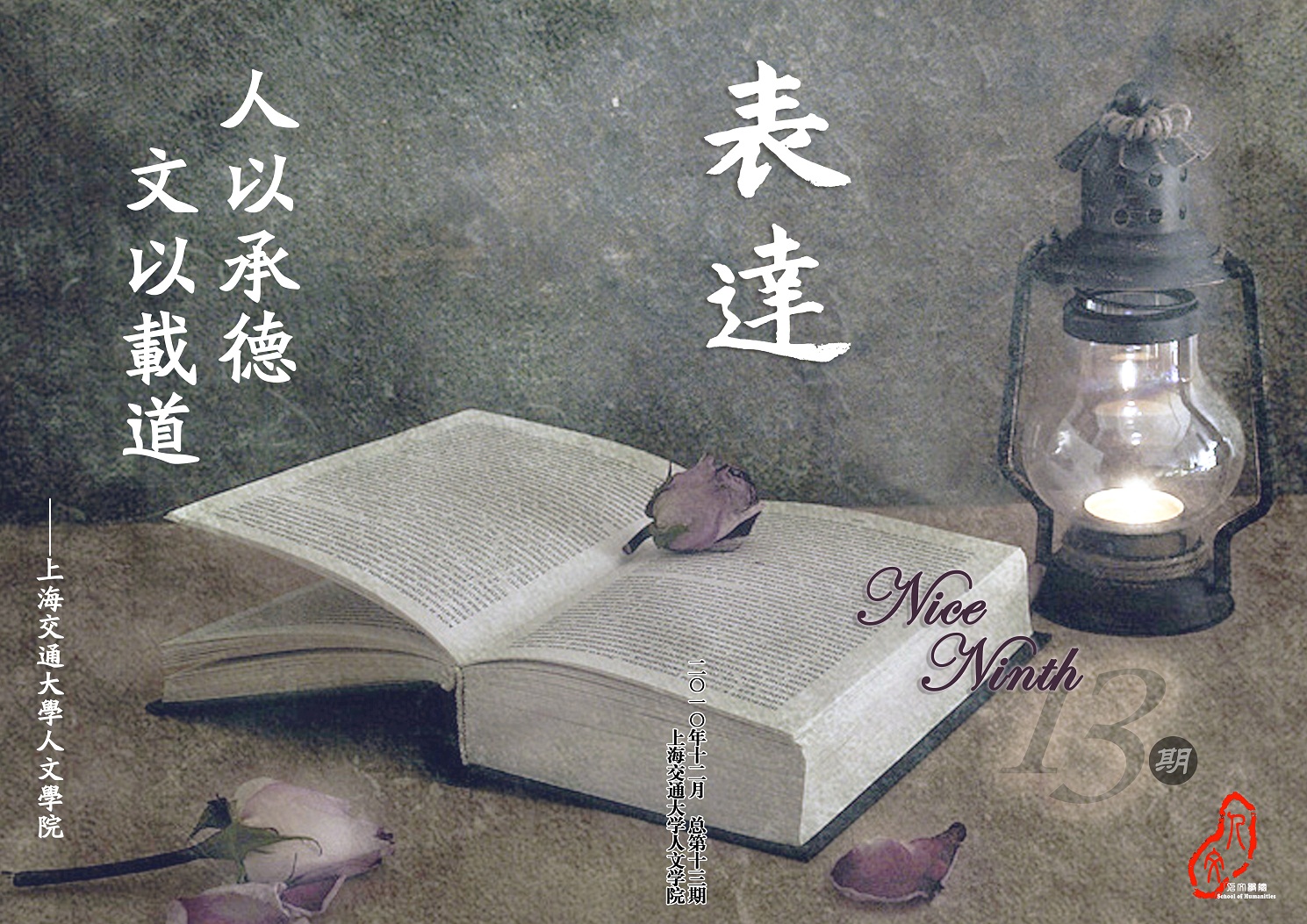
第13期表达封面封底
好不容易有机会写一点什么,就多写一些好了。比如饮水思源要站庆了,然后这第一十五届站庆用的是自己做的Logo,也算是在交大生涯留下了一点“历史”。绘图板用的不畅,也没大工夫磨时间在这上面,就画一个粗稿坐等修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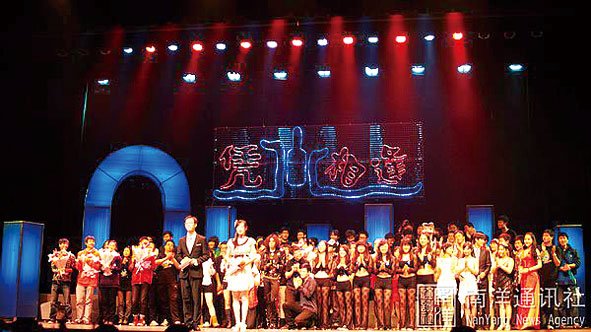
教授大都也是明眼人,我心里也能掂量自己到底几斤几两。所以还是让自己重一点吧,小时候不喜欢吃的玩意儿长大了不都能接受,有些还变得喜欢吃了麽?
就好像刻意为了营造出社会和谐的气氛,大家都“莫谈国事”。然后自己这儿“莫谈学习”。藏着掖着总也不好,不过社会水太深,若是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这片“浅水区”大家都来掀桌子就不好了。况且说到头来定方向这件事还是不敢做一个“了断”,说是EE总还放不下CS那边的一点点。虽然看起来EE的老师也都对码农或者编程什么的略带轻蔑之情,可能自己也有吧,但除了这点“外来务工人员”般的“廉价劳动力”自己能出得起以外,身上还真没什么可被剥削的了。
四月踏一次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叹。毕。

